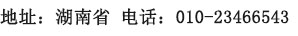新京报讯(记者田杰雄)田园牧歌的生活到底是不是真的浪漫唯美?家住北京新源里的王少晨有自己的答案。他从前是年薪小四十万的广告公司制片人,年后选择成为京郊3个蔬菜大棚的主人,收入却往往不足此前的零头儿。
务农头一年,王少晨赔个底儿掉,三个月在棚里菜花中抓出上万条菜青虫,没找到买家,辛苦种出的蔬菜只能白白扔掉或干脆喂鸡。田园生活原来没有想象中浪漫,可如今的昌平“农夫”王少晨说,整个生命被重启了,“我毕竟接触到了一些真实、新鲜的东西。”
王少晨在蔬菜大棚中。新京报记者田杰雄摄影
怕祸害母鸡“关押”二十多只猫咪
刚走进通往大棚内的第二道门,王少晨的眼镜上被糊上了一层雾气,在这个位于昌平百善镇平均气温21摄氏度的大棚里,这个冬季有十几种蔬菜正等待成熟。
“每个棚的使用面积大概有多平方米,我们目前租了3个。这里边温度还不算高,我们另外种草莓和水果西红柿的大棚里还有4个加热风机,温度能达到24摄氏度。不过就是贵,一晚上要走块电钱。”
蔬菜大棚里的加热风机。新京报记者田杰雄摄影
王少晨说的这两样产品早已供不应求,前两年的许多亏损和投资都指着草莓和西红柿这俩宝贝翻盘。西红柿尤其美味,20元一斤的价格,还让王少晨欠了一屁股“债”——订单源源不断,但产量并不是总能跟得上,“有时候我们在藤架间走动,时常弯腰间一撅屁股就碰掉三四个,只听吧嗒‘20块钱’掉地上,也是一阵儿心疼。”王少晨一边提醒进棚前来参观的人别怕麻烦,及时增减衣物,一边等着眼镜上的雾气慢慢退去。
年是王少晨从制片人跨界到农夫的第三年,除了有满棚满地的蔬菜水果,与大棚一条乡间小道相隔的区域,几乎也成了小小的动物园。门口的土狗每每遇到生人经过,免不了不间断地狂吠;曾经用于简易加工的小工棚里,现在已经成了二十几只猫咪的栖身之所,每只都被“关押”得胖胖的。百米开外,三五百只鸡正在闲庭信步,不远处几十只鹅见有人来,聒噪声也是不绝于耳。王少晨经过时会说,“从来都不知道哥几个聊什么。”
王少晨饲养的鸡在冬日阳光下漫步。新京报记者田杰雄摄影
养动物并不是农夫王少晨的爱好,这里每一样动物的出现都称得上“事出有因”——身份转变之初,几百颗鸡蛋算得上是他稳定收入来源之一;地里的鹅是土地所有人提出饲养的;而旁边的猫和狗则是由于曾经组团儿来祸害过地里散养的母鸡和小鸡,王少晨干脆将他们圈养了起来,还为十几只猫做了绝育,“每天除了在地里转,也少不了定时定点来喂它们。有时候喂晚了,刚走到门前就能听到它们聚在一起‘骂’我。”
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这大概算得上许多城市人向往的田园生活,但作为这一切的拥有者,王少晨说田园其实根本没那么浪漫。
抓了上万条菜青虫 年赔个底儿掉
年的他身材圆滚滚的,一张嘴便能听出是四九城的口音。除了一身衣服在狭窄的大棚过道内蹭着砖墙沾上了些土,王少晨看起来与城市人眼里传统的农民形象相去甚远。
但他现在又确实是每天与泥土、蔬菜打着交道,只不过是“半路出家”。在年以前,他是广告公司的制片人,个人年收入小四十万,算得上是这座城市里的中产。年之后,王少晨的生活则与自己的前半生完全脱轨,投入的资金与自己曾经的年收入不相上下,收入却只有三五万元,到如今也依然在赔钱。他乐此不疲,说很幸运,不后悔。
“最初只是想尝试玩玩这些东西,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发现种植确实不太容易上手。”隔行如隔山。从阴雨天气里自己连大棚卷帘都盖不利落,到三个月在棚里菜花中抓出上万条菜青虫,行业的陌生和困难让这位城里人完全始料未及。现实残酷,在他踏入郊区农田的 年,就赔了个底儿掉,因为没有销售渠道,几千斤的蔬菜只能白白扔掉,或者干脆就成了自家几百只鸡的美餐。
情况直到有消费者偷偷把蔬菜送到特别严苛的检测机构抽查,这才有所好转。发现蔬菜质量居然远远高于国家标准,农场附近 社区的住户们挺惊讶,于是建立了百余人的买菜群,为当时的王少晨的大棚蔬菜销路打开了一扇门。
刚刚采摘的西红柿准备包装发快递。新京报记者田杰雄摄影
“只有适应不美好,才能开始接受乡村”
“城市人永远不会知道真正的乡村是什么样。”王少晨坦陈,每天跟蔬菜和土壤打交道的生活,其实并没有许多城市人眼中看到的那么美好。“我最初想象中的农场乡村可能还停留在山水田园,农场里都是美好,可能有鸡在跑,或者在阳光普照下菜都自然而然地长得很好。”但美好的想象总会被现实打脸,对事物的感情和喜爱需要一点一点积累。
王少晨说,城市的人不会想到菜地里的虫子其实多得令人跳脚,不会直面所有付出几乎因为销售问题而付之东流的窘况。“可这又都是真实的生活。只有当城里人看到不美好的东西,才是城里人适应乡村,接受乡村的开始。”他相信,无须谈情怀,还要将所有对田间的畅想抛诸脑后,只有回归到现实生活当中,才能出现真正的城乡交流,“无论是个人还是媒体,如果把农场农庄和田园生活天天搞得特别理想化,那么只会把乡村和城市之间的距离推得越来越远。”
过去不值得紧张现在不需要回头
王少晨说,他并不是一个在城市生活里‘逆行’的人,“你看我胖乎乎的,其实最初只是喜欢采摘,吃东西。一直有想了解自己喜欢吃的这些东西是怎么种出来的,后来有了机会,一合计,那就干这个吧。”总结原因,王少晨并不想赋予自己转行的决定有其他别的特殊意义,往简单说,他只谈“想从原来圈子跳出来,接触一些真实的东西”。
王少晨回忆,自己当制片人期间的工作强度大,基本没有时间吃饭,所以练就了18秒内吃光一个板烧鸡腿汉堡的本事。达成职场成就的同时,也让生活变得麻木,食物只是满足生活最基本的需求,王少晨总觉得自己丧失了对事物感觉、反馈的能力。直到后来,走进农场,每日期盼着、检测着水果西红柿的甜度,才让王少晨找回一些生活的希望和真实滋味,“觉得自己在创造”。回想原来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他说会觉得之前“紧张得特别不值得”。
蔬菜大棚里的羽衣甘蓝。新京报记者田杰雄摄影
鲜衣怒马和奔波忙碌早已烟消云散,眼前的路倒是能看到希冀的光。曾经的工作中,同事或是合作伙伴相互之间习惯称彼此为“老师”以显恭敬,而现在在多人的买菜群里,王少晨和他的消费者都爱开玩笑似的自称、或是喊他一句“地主”。曾经的圈子里,所有人都在意体面,采购大几千元的衣服、上万元的箱子稀松平常,就那样还老担心不够新款,而如今的农夫已每日在田间灰头土脸,一心务农爱自由。
现在,这个名为“羽田生活”的小农场已有着稳定的消费群体。偶尔逢假期末尾,王少晨会在朋友圈小小嘚瑟一下:务农的生活让他逃开了过去上班时如影随形的间歇性头疼,也让夫妻二人有更多自由的时间陪伴一岁半的小娃娃。
年,王少晨刚刚踏入农场生活不久,曾发过一条朋友圈:“自由是年轻的时候敢漂泊,长大的时候能回家。每当刚开始一段新的事情,总有一段不真实的感觉,就像生命的重启,再次把苟且抛向远方,哼唱着新的诗句,带着彷徨与快乐再也不回头。”
到如今,“不真实的感觉”逐渐消散,这个三十多岁的新农夫一头扎进他心中的桃花源,渐行渐远,不会回头。
新京报记者田杰雄
编辑张牵校对柳宝庆